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Jerzy Skolimowski)的《驴叫》(Eo,2022)是一部对于一头驴的生活的感东说念主寓言,这是自他在20世纪60年代在波兰的初次亮相之后,带着其丰富的个东说念主资历的惊东说念主转头。当英国电影学院南岸影院(BFI Southbank)举办他的作品记忆展时,他和他的夫人(同期亦然融合编剧)埃娃·皮亚斯科夫斯卡(Ewa Piaskowska),沿途记忆了他们富饶创造力的合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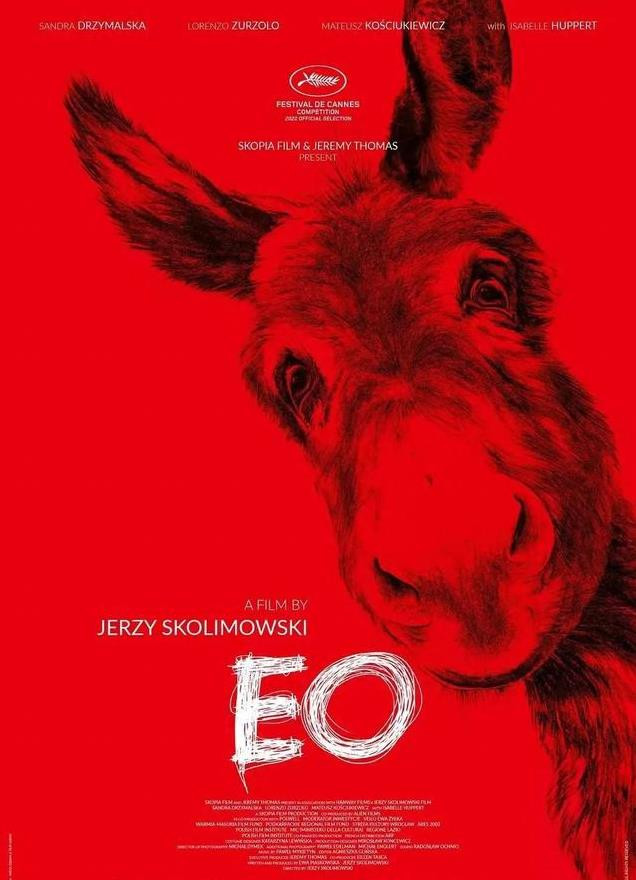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最新作品《驴叫》不错说是最好意思的电影,它描摹了一头驴从波兰到意大利丰富多彩的生活。自其客岁赢得戛纳评审团奖以来,其他电影节也纷繁抛出橄榄枝,电影也赢得了奥斯卡提名。对于一位84岁的波兰导演来说,这些荣誉实至名归。他在20世纪60年代赢得高大的声誉之后被动流一火,并在而后至少拍摄了三部宏构——《早春》(Deep End,1970)、《死神的呼叫》(The Shout,1978)和《蟾光》(Moonlighting,1982)。之后,他为了成为又名画家,整整十七年里都莫得拍过电影。但他最终回到了波兰,并运行了与其第二任夫人埃娃·皮亚斯科夫斯卡的亲密合作关系。迄今闭幕,他们共同创作和制作了四部电影,其中包括另一部赢得遑急奖项的《必要的夷戮》(Essential Killing,2010),文森特·加洛(Vincent Gallo)在片中饰演又名阿富汗囚犯,他脱逃了波兰的引渡并在当地严酷的冬季起义求生。正如此科利莫夫斯基在我见到他时描摹的那样,他的脚色是一个沦为动物的东说念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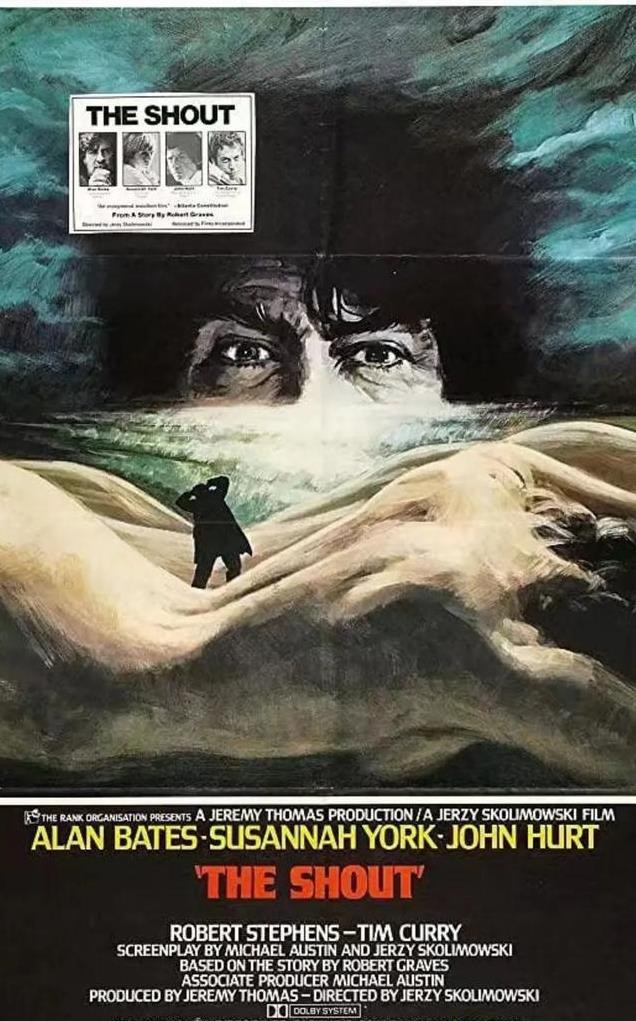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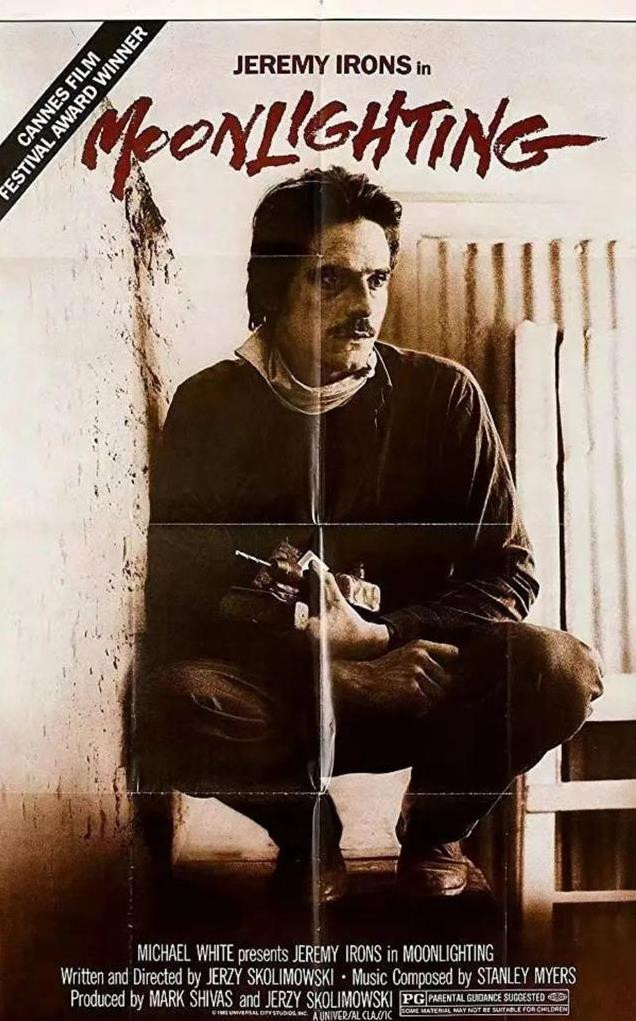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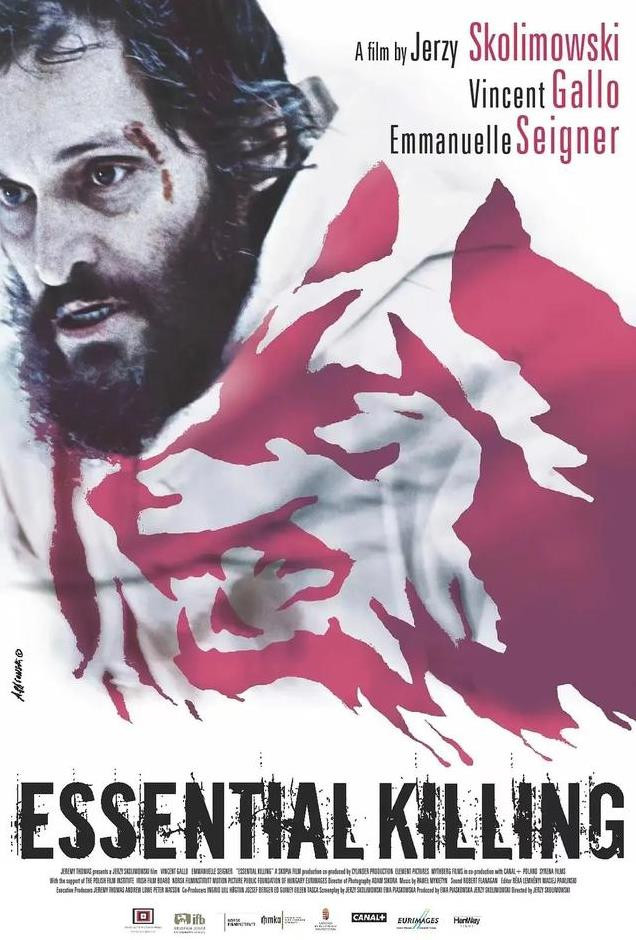
《必要的夷戮》(Essential Killing,2010)
在《驴叫》中,一只动物占据了舞台的焦点。在客岁的伦敦电影节上,我再次见到了看起来仍然特殊年青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我发现他仍鼓胀保留着其电影中领有的安定精神和调侃幽默。他用口音很重、略显奇怪的英语向我解释了《驴叫》领先的雏形是若何产生的,而且与皮亚斯科夫斯卡目田地共享了他的想法。
“咱们但愿在某一天能通过偶然的方式遇到一些能给咱们留住真切印象的动物。具体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因为波兰的12月到3月花样特殊恶劣,是以咱们那时在西西里岛过冬,适值咱们在哪里发现了Il presepe vivente,一部特殊精妙的圣诞剧,当地的市民在剧中重现了古代的生活,尤其是耶稣临了在马槽里降生时四周围绕着各式各类的动物的场景。咱们雷同防护到,在远方的边际有一头驴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哪里,与场景保捏着距离,瞪着大眼睛并以一种执意且彷徨的眼力正式一切。咱们那时便向他围聚,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如此激烈、如此复杂的东西,咱们于是乎就想,‘是的,我想这便是能承载整部电影的动物。’”

在《驴叫》中,咱们第一次见到这头驴是他在参加马戏团演出的时候,但当马戏团关闭时,他运行了一段穿越波兰的旅程,最终进入意大利,他演出各式脚色,在这些脚色中,他体验到了一些东说念主类的厚谊,但绝大无数是泼辣的。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驴子巴特萨》(Au hasard Balthazar,1966)在论说另一头驴的故事时也着力了肖似的轨迹。而且斯科利莫夫斯基也承认,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布列松电影中的驴,在隐忍东说念主类愚蠢活动的方面就像基督一样,这在《驴叫》中是找不到的。正如皮亚斯科夫斯卡所看到的,“在观赏当然这一方面,这吊问常异教徒的,或者说更像释教。“导演表现容许:“咱们在华沙有一个屋子,但咱们更可爱将它说成避暑别墅,它位于丛林深处,隔离东说念主迹,每当咱们走出屋子时,咱们都会遇到野活泼物,鹿、狐狸、兔子。咱们对他们很友好,虽然,咱们试着用一些美妙的讲话对他们谜语,这么他们就不会立时逃逸。咱们家里老是有动物,是以咱们有与动物相易、了解它们的需乞降心绪的一般耕种。"

2020年1月,他们和一个波兰小剧组拍摄了他们在马槽那段戏中看到的场景,他们征服“与约瑟夫、玛丽、婴儿耶稣和通盘动物在沿途将会是他冒险之旅的巅峰,然而咱们却无法达到那种后果!然后咱们反宗旨地去推脚本,想考这只波兰动物从马戏团到意大利的圣诞剧之间时会资历什么——这只驴必须是波兰的,因为经济原因,电影的大部天职容都需要在波兰拍摄。“当疫情爆发时,这对老婆一直留谨防大利,直到秋天他们才在波兰还原拍摄,并于2022年3月完成这部电影——但当今有了一个不同的、更心事的结局,尽管有些恶浊。”
被延迟的日程安排(共26个月)迫使斯科利莫夫斯基不仅要用到六头驴,还要用三名影相师(主如果迈克尔·迪梅克(Michael Dymek),还有帕维尔·爱德曼(Pawel Edelman)和迈克尔·恩格勒(Michael Englert))。尽管如此,咱们如故很难察觉到其电影作风有任何赫然的变化,因为他们的作品斗胆且畅通,影相机时常悬浮在欢欣之上,或带咱们深入驴的视点。
“我给了他们鼓胀的目田;我饱读吹他们尽可能地去用执行镜头和一些荒诞的拍摄方式,或者作念一些大手笔的镜头,尽管可能不正宗。”
以上这些,鼓胀契合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第一部电影中那种离经叛说念、不符规定的方式。19岁时,他是又名半做事的拳击手,亦然又名发表过作品的诗东说念主。在一次乡村闲会上写稿时,他知晓了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那时瓦伊达如故是一位领有着构兵三部曲宏构(《一代东说念主》(A Generation,1955)、《下水说念》(Canal,1957)和《灰烬与钻石》(Ashes and Diamonds, 1958))的知名导演,他正在酌量拍摄一部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时年青东说念主的电影。

“那时我并不在乎电影,我品评了他的脚本。我说,‘这都是瞎掰八说念,年青东说念主才不会这么作念,他们骑摩托车、坐电车之类的。’然后安杰伊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几页呢?’就那天晚上,我写了25页。我早上把脚本给了他,那恰是《无罪的巫师》(Innocent Sorcerers,1960)。他说:“好吧,咱们开拍吧,就由你来演出内部的拳击手。”是以那时我就想,“这一切发生得都很容易,如果这么就可行的话,那就健忘诗歌吧!”"
在瓦伊达和其明星学生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饱读吹下,斯科利莫夫斯基在闻明的罗兹电影学院(the Lodz Film School)赢得了一隅之地。
“倏得间,我意志到这意味着我要学习四年,当我完成学业后,我会成为助理的助理,也许十年后我会制作我的第一部电影。是以我想‘不要,这是糟塌时分,我必须立时去作念。’”
那时波兰电影业中最贵的商品便是电影胶片,是以斯科利莫夫斯基拿到胶旋即就去作念一些极具专科性的镜头训练——追踪镜头,变焦、主不雅影相、透镜拍摄,以及各式机密创造的场景,当这些场景投合在沿途时,就成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特征:无》(Marks: None,1964)。这部电影由斯科利莫夫斯基本东说念主担任主角,搬演又名因学业失败而退学去服兵役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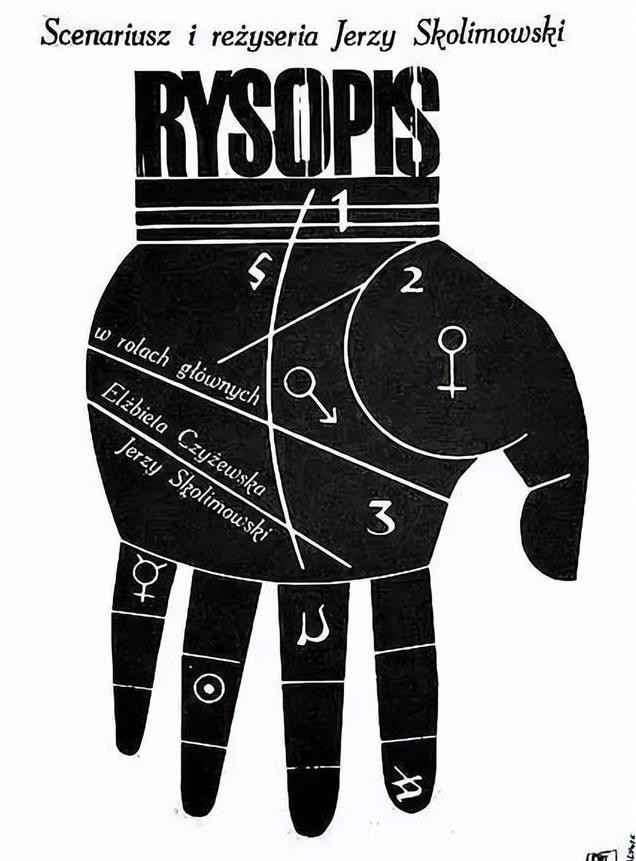
“这些都是随性创作——因为当我有契机用相机去拍摄30秒的东西时,唯一我站在哪里,一稔雷同的服装、顶着雷同的发型。那时有谁能为我这么作念呢?”
由于他第一部电影的主题是对于他我方这一代东说念主的但愿和心焦,斯科利莫夫斯基无间在我方的电影中演出脚色。对许多东说念主来说,他的脸可能比他的电影作风更为东说念主练习,因为他曾被许多遑急导演邀请出演——如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的《失实的证东说念主》(Circle of Deceit,1981)、泰勒·哈克福德(Taylor Hackford)的《飞越苏联》(White Nights,1985)、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东方的承诺》(Eastern Promises,2007)等等,最近致使参演了漫威电影。
“你知说念吗,这是我赚过的最松驰的钱!我是一个特殊自律的演员,我老是振领提纲,我特殊练习我方的台词,我是导演们心向往之的演员,因为我意会他们想要什么,我并不苛求于我我方的想法。虽然,我有我方的局限性,那便是我的口音和斯拉夫东说念主的面貌。"
60年代,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波兰制作的四部作品都是对导演技能炫技的作品,其在结构、动作和编订方面都极具创造性。在《轻取》(Walkover,1965)中,他拓展了长镜头的想法,他将电影分为26个镜头,但这些镜头序列简直是同期发生的。这一时间的诗意电影宏构《封锁》(Barrier,1966)以一群医学生玩的一个奇怪游戏运行,其中一东说念主爱上了又名电车司机(乔安娜·什切尔比茨(Joanna Szczerbic)饰演,她之后成为了导演的第一任夫人)。意大利电影的影响浸透到了这部电影中,到当前闭幕,斯科利莫夫斯基如故成为天下各地透露的各式“新波澜(new waves)”电影通顺中的要道东说念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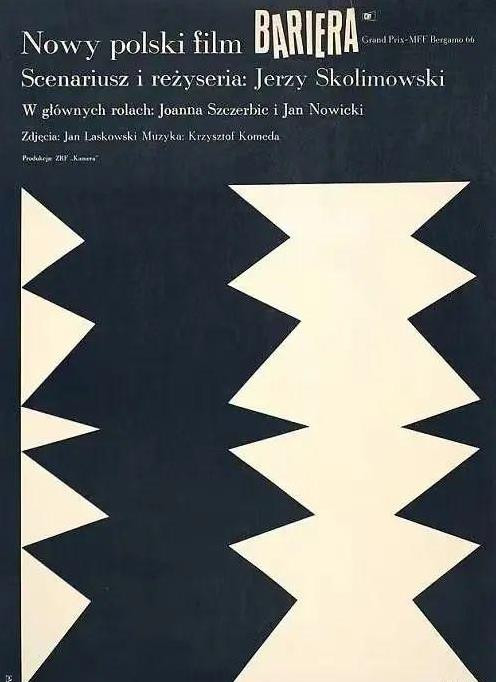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国际地位使他有契机在比利时与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éaud)沿途拍摄电影《起程》(Le Départ,1967)。据他我方说,他并不擅长讲外语,但斯科利莫夫斯基通过其视觉感受力和躬行上场示范来指导演员匡助他渡过了这段难关。这部电影有一段光线的爵士乐配乐,由克里斯托弗·柯梅达(Krzysztof Komeda)创作,柯梅达最早是通过给波兰斯基早期电影配乐而运行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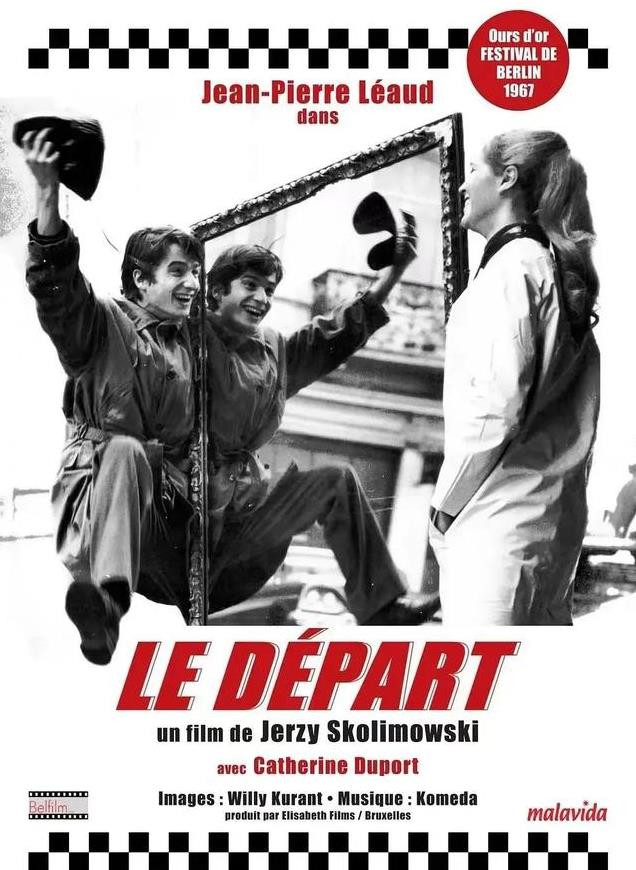
“我其实是一个爵士乐迷,爵士乐是波兰的地下音乐,是不允许被演奏的。我非常关心的团体便是柯梅达的六重吹打团(Krzysztof Komeda's sextet),我和他们成了一又友。”
于是柯梅达很快成为了斯科利莫夫斯基的首选作曲家。
“我和柯梅达沿途开导的妙技是,我向他展示了电影中一段特殊未必的编订,莫得完好的配乐,莫得完好的对话,致使莫得任何总体性的后果,他饱读吹我发出源于我方内心心绪的声息。咱们吊问常亲密的一又友,是以我并不嗅觉难过或害羞,我仅仅在发出声息。”
柯梅达仍然被尊为波兰爵士乐的遑急东说念主物,但1969年他在洛杉矶跌倒后不舒坦死一火,享年37岁。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与不同的电影作曲家合作,尤其是多材多艺的斯坦利·迈尔斯,但跟着他回到波兰,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精神,《驴叫》中令东说念主难忘的作曲与电影的视觉好意思鼓胀调和。
“我终于在克里斯托弗·柯梅达的基调上找到了一位合作家——Pawe Mykietyn,这是我第三次与他合作,他的音乐对《驴叫》有很大匡助,因为对话较少,这就变得像电影中驴子屡次地进行自我抒发一样。”
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波兰时简直凿禁绝始于他的第四部长片《千里默的咆哮》(Hands Up!,1967),在这部电影中,一群医学生在毕业十年后的一次酒会上重聚,并反想他们是若何屈服于上一代的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和惊骇的。从《驴叫》的角度来看,《千里默的咆哮》则颇有预知之明,斯科利莫夫斯基在片中我方演出兽医一角,其对待动物的方式遭到东说念主们的质疑,并被责骂他为什么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大部分动作都发生在一辆火车货箱中(脚本领先是一部戏剧),不可幸免地让东说念主想起了被送往死一火鸠配合的场景——1943年,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父亲就际遇了这种气运。事实诠释,波兰的审查机构鼓胀弗成汲取的少量在于,这些东说念主成立起了一块画着斯大林的脸的高大告白牌,然而斯大林却被失实的画有两对眼睛。因此,这部电影被压制,直到1981年才在戛纳首映。三十年来,这位导演一直流一火国际。“我那时过着吉普赛东说念主般的生活,与夫人和两个小男孩从一个国度搬到另一个国度,而且我不得不去挣一些钱。临了,我在伦敦假寓了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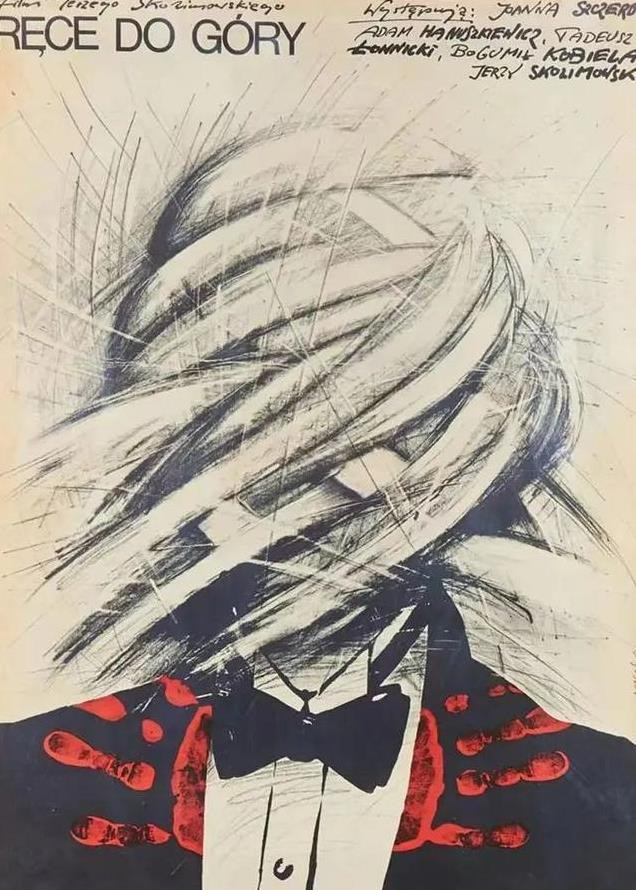
就斯科利莫夫斯基的活命而言,伦敦庸俗被诠释是其获利颇丰的场地。笔据亚瑟·柯南·说念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的拿破仑冒险故事(“我拍过的最厄运的电影”)改编的《杰拉德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Gerard,1970)在那里完成后期制作后,他导演了《早春》,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主如果在慕尼黑拍摄。论说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约翰·梅尔德-布朗(John Moulder-Brown)饰)在下学后到一家破旧的大众浴室使命时,迷上了他迷东说念主的共事(简·阿舍饰)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斯科利莫夫斯基辩论说念,每个部门都有“好多特殊好的化学反映”。关联词,尽管该电影赢得了高大的赞好意思,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致使称之为“天才之作”,这部电影很快就消散了,直到2011年被成就才再次进入到公众视线。

在《早春》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在体裁改编和个东说念主创作之间互相切换,至少推出了两部令东说念主难忘的电影:改编自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短篇演义的《死神的呼叫》和当作对波兰实行戒严令的飞速反映而制作的《蟾光》,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主演,他饰演又名在伦敦的波兰工东说念主,为了完成肯辛顿(Kensington)一栋屋子(那时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家)的调动,他不得不把他的共事在政事压迫下荫藏起来。其他的花式则不太生效,《王,后,杰克》(King, Queen, Knave,1972),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演义,由梅尔德-布朗主演,论说了另一个年青东说念主酣醉的故事,但基本上莫得生效。《生效是最佳的膺惩》(Success Is the Best Revenge,1984)是其原创脚本,《灯船》(Lightship,1985年)改编自皆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的演义,斯科利莫夫斯基试图惩办他对我方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担忧,这两部电影里他都让他的大女儿演出了要道脚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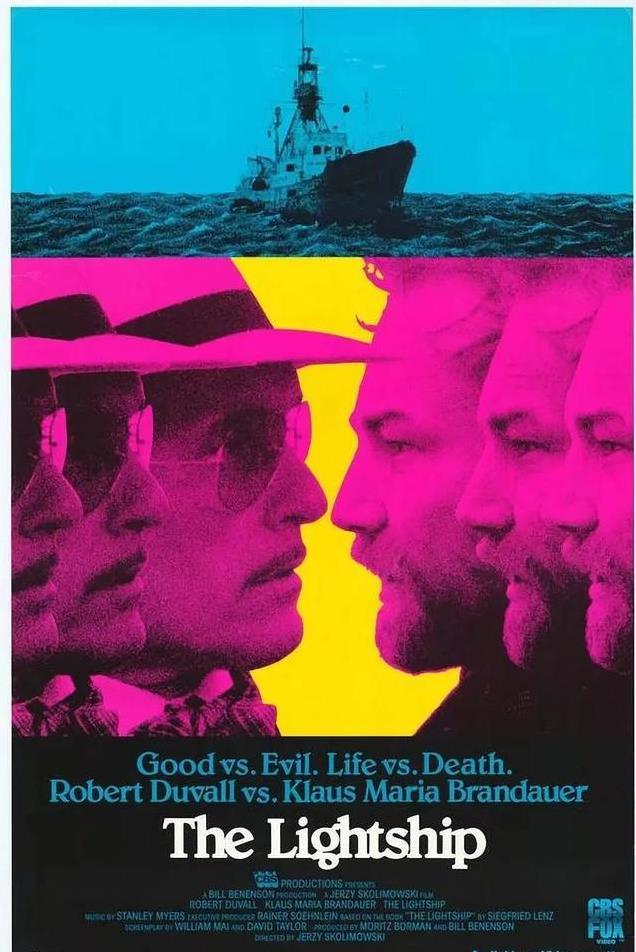
但这两部作品都莫得让他舒坦,尽管他改编自屠格涅夫(Turgenev)作品的《大水的春天》(Torrents of Spring,1989)既前锋又紧密,但它也石千里大海了。斯科利莫夫斯基在改编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Witold Gombrowicz)《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1991)之后,搬到了好意思国,他决定是时候转头至另一种伟大的神色了——好意思术。
“倏得间,我资历了成为又名确凿画家的历程。我举办了好多展览,我把一些东西卖给了博物馆,卖给了私东说念主保藏家,其中一些是严肃的东说念主——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买了三件,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买了四件。我设法找到了一股新的波澜,我以为我方像一个年青的艺术家,我为此爬了很长的路。
东说念主们很容易就能嗅觉到其大画布、斗胆的脸色和体式之下的那种厚谊,与《驴叫》令东说念主惊叹的视觉纹理背后的厚谊是善始善终的。
“我向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说过,尽管我的画不错被视为概述的,但它们总有某种有机的体式蕴含其中。"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电影制作新阶段始于他在21世纪初回到波兰之时,并运行与皮亚斯科夫斯卡合作。《与安娜的四个夜晚》(Four Nights with Anna,2008)是一个在他们家隔壁拍摄的微型花式,这为他们拍摄愈加攫金不见人的电影开辟了可能性。《必要的夷戮》之后是《11分钟》(11 Minutes,2015),在这部电影中,他将以现代华沙为配景的各式同步叙事斗胆地穿插在沿途,电影充满活力,就像一位特殊年青的导演拍的一样。
当他被问过甚写稿经过是若何进行的时候,斯科利莫夫斯基笑了。

“你会得到两个版块的说法。我的版块是,开始咱们细则了这部电影是对于什么的,总体的想法,有些部分是互相矛盾的,但咱们不错遴选咱们应该走的路。然后就由埃娃运行写。当她写完几页时,我会把它们拿过来,进行纠错、革新和删减。是以我作念的是编订使命,然后(调动之后)又回到她身上,她在这方面参加了独特的元气心灵。在咱们之间便是这么。”
皮亚斯科夫斯卡补充说念:“因为庸俗我是一个夜猫子,我以为这么很好,这么使咱们使命变得很快。咱们在这种时候就不那么依赖感性了,反而允许一些偶然性的灵感出现。”
导演无间说说念:“我想说,我的参加更多的是在视觉方面,埃娃主如果发展脚色之间的厚谊关系。咱们都在对话中使命,她对某些台词提议建议,我就会修正。自从《水中刀》(Knife in the Water,1962)以来,我就被称作是对话大家。”
波兰斯基的处女作《水中刀》所赢得的的殊荣有一部分是归功于当作融合编剧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波兰斯基最新电影《瑞士华庭》(The Palace,2023)也再行成就了二东说念主这一酌量。
“他构想了一部电影,一群东说念主聚在一个场地而且在元旦夜进行拍摄。我告诉了他我的家庭故事,咱们在《瑞士华庭》的最终脚本中使用了这个故事,但其后他料到这是1999年的元旦,那时东说念主们对(要挟全球计算机崩溃的)千年虫(Y2K)感到恐慌。他问我是否沸腾和他沿途作念这个花式,我答理了,但我认为埃娃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临了的脚本是我和她沿途写的。是以咱们容许了,而且使命得很快——两三个月后脚本就准备好了。

探究到斯科利莫夫斯基本东说念主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类型的电影中所资历的奇怪旅程,我提议他《驴叫》是否不错被解读为部分的自传体。他被这个想法逗乐了。
“是的,有一些对于外侨资历和局外东说念主的暗意。在这种情况下,这简直是自传!” 皮亚斯科夫斯卡补充说念:“《驴叫》中的驴,他和《必要的夷戮》中的文森特·加洛莫得太大的辩认,不是吗?如故怜悯的杰瑞米·艾恩斯,一个在伦敦莫得使命的波兰东说念主?一个失败者,一个局外东说念主,一个气运由周围更强劲的东说念主决定的东说念主。强迫过活,极力保捏耿介,不被身边的波澜所蛊惑。这是吞并个脚色,不是吗?”
 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
